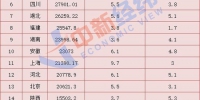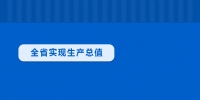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
在北京打工的小张在黑龙江老家参加了新农合,可是在北京打工得病后不得不回县里看病,因为城里的医院无法报销,很不方便,这样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国务院批准2014全面深化改革七大重点任务近日公布,其中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从各地实际出发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全部常住人口的时间表。政策落地有声,接下来是怎么尽快执行的问题。围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财政部一直在努力,这其中都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还将如何做,记者专访了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王泽彩。——编者
王泽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长期专注于公司治理结构、财政政策、预算管理制度研究。先后出版了《企业家职业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部门预算管理》等7部著作。牵头或参与研究世行、亚行和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30余项。
杨光:最近,看了您和您的团队搞的关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调研报告,感触颇多。因为这项工作是财政部一直努力推的,比如新农合就是一项很有代表意义的举措。
王泽彩:除新农合外,目前主要还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从2009年实施“新农保”以来,到去年底全国“新农保”覆盖了1.8亿人。今年2月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至此完成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即“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在一起,成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前不久,财政部又出台政策,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和居民医保人均补助标准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40元,达到320元。农民和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20元,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90元左右。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言,其待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基础养老金”。目前,发放标准是年满60岁老人,每月55元。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允许,可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比如,北京等地在月均55元基础上,由地方财政筹资提高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这个完全取决于农民和城市未就业居民缴费的多少。按现行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从每月100元到上千元不等,缴费标准差别甚大,而且完全基于自愿,实行多缴多得,少缴少得。此外,农村还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低保,且低保标准已经日趋接近。例如,江苏省已全面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省内城市低保平均标准达到每人每月480元,农村低保平均标准达到每人每月410元。
再就是义务教育。2008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教科书和作业本全部免费,从而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均等化。
杨光:国家在致力于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上已经迈出了卓有成效的步伐,但我认为距离农民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你认为,彻底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有哪些障碍?
王泽彩:主要根源于体制问题。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种“城市偏向型”的非均衡制度安排导致了城乡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例如,城市的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城市里实行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农村实行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保障层次更低,手续也更为繁琐。另外,不尽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阻碍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障碍。实行分税制后,财力不断向中央集中,而一些涉及全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却从中央层层下移,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对等。比如,我国对城乡居民养老,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投入,而地方又以县级投入为主,在县级财力普遍不足且偏重县城的现状下,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障一直低位运行。虽然针对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中央采取了转移支付的政策,但目前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过低而专项转移支付比例过高,造成了基层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难以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杨光:进城但未落户的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独有的群体,这一群体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尤为壮大。你在报告中提到,江苏存在着1900万“两栖”人口,往返于城乡之间。像这样的一个群体,没有城市户籍的情况下,生活就很艰难,也很不公平。
王泽彩:是啊。户籍制度的本质不单是一纸城镇户口,还有户口背后的资源、福利与权利,即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因此,要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且长期得不到扭转的问题,最终还是要打破二元结构体制。
杨光:那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问题不能只是财政的问题吧?
王泽彩: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由谁来负担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政府、企业和农民都是成本负担的主体,任何一方不愿付出,即便是改了户籍,市民化改革的初衷也不能实现。一个进城农民工要享受市民待遇,按现行政策,要由政府支付的那部分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包括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社会救助、医疗、就业等成本,在城里打工的农民,一旦得了病只能回乡看病,新农合在城市医院行不通。
杨光:对,我认识的一位打工妹就告诉我,她在黑龙江老家参加了新农合,可是在北京打工,得病后不得不回县里看病,因为城里的医院无法报销,很不方便,像这样具体的问题,要克服哪些制度上的障碍,有无具体的解决方案?
王泽彩:我认为,制度安排上的障碍主要有两点:第一,针对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主要分三种,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因三种保险之间无法相互衔接,致使医保制度呈“碎片化”状态。而且,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而新农合由卫生部门管理,财政部门仅仅对分配过程加以监管,形成“多头管理”现象。从学术研究到实践工作,实施并轨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先行并轨,然后再并归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另一种是,先并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然后在城镇化进程完成后再并轨新农合。截至目前,天津、青海、山东、重庆、广东、宁夏、浙江等七个省份已启动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的改革试点。第二,新农合本身的信息认定问题。目前,新农合仍然不能实现跨省报销。对于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的医疗报销,国家卫计委称,我国正在建设新农合的信息化系统国家级平台,将来农民工到任何一个跨省的医疗机构就医,信息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对农民工报销提供了方便。据国务院医改办消息,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在江苏、北京、内蒙古、吉林、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部分省份试点跨省就医即时报销办法。如江苏省从2011年就开始全面实施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即时结报改革,特别是徐州市2010年已探索实施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机制。
对于您提到的在北京的打工妹而言,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只能等到新农合跨省报销政策出台为止,然而即使新农合可以在北京报销了,其报销比例仍然会低于在县级医院的比例,因为新农合制度设计的本意就是希望大部分的医疗在县级完成。第二种解决方案,就是在北京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杨光:但在北京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外地农民,怎样才能转换医疗保险,有何详细的制度设计?
王泽彩: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有制度层面的保障,尤其应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一是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方式。目前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在现行财政体制中固定为常态化的财政支出,更多地停留在一年一拨的专项补助形式。将来应将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列入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计算公式,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内容。二是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是通过因素法以公式的形式进行分配的,必须完成诸如人口数、服务标准、特殊影响因素等综合信息的收集与整理,这是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实施,也必须依赖前期大量科学有效的统计工作,并逐步形成科学规范、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库,完成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基础工作。三是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体制调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正向激励的导向,做得好的地方不但能够足额拿到转移支付资金,而且还可以获得必要的奖励。对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金额也应与农民工目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挂钩,促使地方政府以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更多的转移支付,实现正向激励。
杨光:农村留下来种地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他们除了留守耕地,还为子女看守着仅有的家园,这部分人的养老就医该怎么解决?如果留守农村的人有了养老就医保障,那么他们的子女,那些进城打工者,最终会有一个期盼——他们在城里混不下去时能有退路,这最终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这是否应该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方面,对于这部分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怎么体现?
王泽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制的案例。对这部分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方案设计,就是要将他们全部纳入一个统一的全民社会保障网络中来。现在的方案是农村养老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且大部分地区实现了保险的全覆盖。然而,这些保险只是形式上具备,从保障能力上来说,还远远不能保障农村居民的安居乐业。无论是“城乡保”还是“新农保”,与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相比,仍然差距巨大,与机关事业单位保障相比更是天壤之别。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险责任是保基本,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我认为,今后发展思路应该是,逐步实现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并轨,不断缩小不同户籍、职业人群间享受保障的差距。这就需要国家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大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各级财政要逐步增加预算内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以及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以补充社会保险资金的比例。